七彩神仙烟,爆珠黄鹤楼是什么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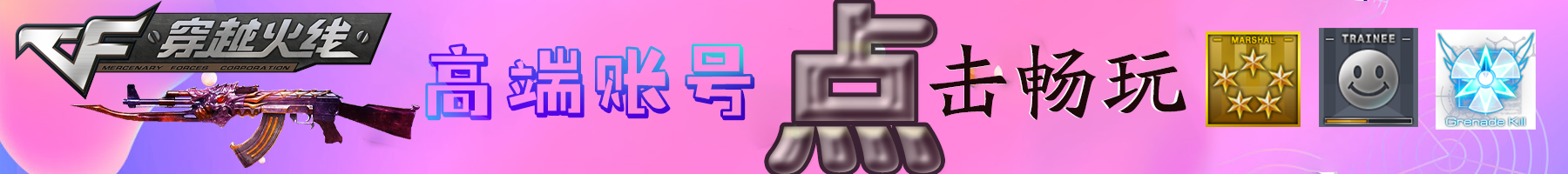
七彩神仙烟,爆珠黄鹤楼是什么珠?
黄鹤楼(硬为了谁)
价格:100元/包

黄鹤楼(硬为了谁)中的爆珠被称为神农珠。从神农香菊中提取的香味,烟里的“神龙珠”有股果香味,据不是每包都有爆珠。
你的室友能脏到什么程度?
常年不洗澡,印象中唯一几次洗澡是大一的时候,全身都是臭味,上课进教室之后全班人都捂着鼻子(我们是150人的大教室,上课时候30个人都能闻到)。曾经去问院长事情,院长来了句:你是不是该洗澡了(눈‸눈)。
床单两年了根本没有换过,(哦对,有次我们说他,他觉得不好意思了,就把床单……翻了个面……)
他本人还臭脚特严重,几次他把鞋放到了楼层的洗漱间,然后一个楼层都特味儿(别人问这tm谁这么缺德……我都不好意思说是我们寝室的)。
大一的时候他体育游泳,所以周体育课就成了他唯一一次洗洗的机会(我们寝室的大一都拒绝去游泳馆),大二不上游泳之后就没见过水。
他生活特别邋遢,还懒。洗漱都没见过!没见过啊!!!!!衣服臭了继续穿!!!!!!!!曾经我们寝室有个大佬看不过去,把他衣服放洗衣房让人洗了,然后他愣是懒得不去领衣服,隔天领的衣服,等人和他打了一周电话才领回来,更气的是领回来还不晒,就放那,然后几天之后又味了!!!!!!!
我们现在还是室友
有哪一刻让你觉得不寒而栗?
爸爸讲过他小时候,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,让我听的时候,觉得不寒而栗……
那时候,爸爸才十岁左右,大伯刚成家分开单过,小叔还是奶娃。爷爷去大队民兵营长,去公社开会夜深未归。忽然,他被什么东西惊醒,纸窗棂上的破洞,除了引出淡淡月光,还是西北风呼呼的声音。再一听,还是院子西厢房里的鸡没命哭嚎,噗噗棱棱的声音格外清晰,爸爸穿衣就要外出查看,那个时候鸡多金贵!奶奶一个小脚女人,胆小怕事,她一把按住儿子。任由鸡叫嘶鸣,扯的心疼。正在这时,爷爷从公社回来了!也听到异响,他立即进了堂屋,迅速抄起一粗壮铁制上门栓,径直走进西厢房,爸爸有了壮胆人,也尾随而去,奶奶吓得大气不敢喘,只有襁褓中的小叔酣然入梦……爷爷推门而入,月光下一道金黄色闪电一下子跃到门梁之上,嘴里发出闷闷的怒吼,眼睛瞪的像铜铃。那家伙见有人进入,一下子扑将过来,爷爷毫无惧色,抄起墙角的粪叉迎头赶上!几个回合下来,爷爷已经将那家伙按死在墙角,爷爷把铁门栓给了爸爸,爸爸使劲平生力气砸向这家伙脑袋。爸爸说,砸不动啊,比石头都硬。那家伙一直挣扎,怒吼声不绝于耳,渐渐没了气息,爸爸的手臂都酸麻的不听指挥,双腿也哆嗦个不停。天亮了,这家伙身长两尺有余,体肥膘状,最后皮毛还卖了个好价钱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呢,爷爷说是野狸,大概农村称呼,具体是什么,无从考证。就是那个月光,那个父子齐上阵厮杀的场面让人越发觉得神奇。故事发生时间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。当爸爸第一次讲的时候,我也才十岁左右,吓得腿有点软的厉害,后背上发凉,有些不寒而栗,那个时候的爸爸,真勇敢。如果是我,估计真会吓得大气也不敢出。究竟是时代变了,还是人变了呢?你见过最邪门的人吗?
关于“邪门”,我也聊一个记忆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小故事。
在我小时候,家里做着集市猪肉档的生意,我们农村集市都是按日期的,两个赶集日之间就要走村串乡去老乡家里买活猪,因为我们家就是赶集零售的生意体量比较小,有时老乡家养一圈猪十几头,一次性买下不合算,镇上同行们之间经常组队去买同一家的猪,现在看也算团购了哈,那时北乡有一个立诚叔,他是专做市郊猪肉批发生意的吞吐量大,我爸和他刚好两个乡之间行业信息互通,所以两家经常相约一起买猪。
图片来自网络,如有争议请联系删除。这个比较“邪门儿”的人,聊的就是立诚叔和他的叔叔。立诚叔那时年纪三十五六岁上下,正值壮年,头脑聪明人又精干利索,但就是脾气火爆且嗜酒能喝,除了做生意开车就少有清醒的时候,同行里人尽皆知的几大酒鬼之一,有一次我们两家一起在南乡里买了一圈猪有近二十头,我们两家的车都装满满的,肥猪们都得四蹄儿叉着绑了屁股朝下头朝上,立着“一根根”排在车厢里。装完两辆车就往北走,我们家用量小先卸下我家的几头,然后剩下的全是立诚叔的,帮忙他一起运回北乡他家里,一路无话。
到了他家把猪卸完,就到饭点了,立诚叔说啥不让走,怎么也得吃了饭再回,他一边儿吆喝婶儿给我们做饭一边儿从柜子里往外拿酒,又指挥我从冰箱往外拿熟食酒菜儿,我那时才十三四岁我爸又不会喝酒,坐下后我们爷俩就陪着他聊天儿,看着立诚叔自己开喝了,婶儿第一个炒菜端上来时他已经喝完一杯至少三两白酒了,等婶儿三个炒菜做完,他一瓶一斤的白酒就剩下一口了,婶子把汤和热好的馍馍放下,他就喊婶儿去买一捆啤酒回来(那时农村啤酒用包装绳捆,一捆十二瓶),婶说冰箱里还有几瓶呢,他就急了说哪才几瓶,买一捆回来再冰上!婶婶扭头往外一边走一边嘟囔着说昨晚刚买的两捆啤酒,就跟灌耗子洞似的没了。
图片来自网络,如有争议请联系删除。婶子买酒回来刚一进院,就喊我们快出来,新买来的猪从圈里窜出来了好几头正满院子乱拱呢,豁这下四个人赶快把猪往回赶,一通忙乱好容易把猪重新关好,我爸看了眼猪圈说天热大中午槽里没水猪能不窜么,就叫我拿皮管子往猪圈食槽里放水,我找不找细铁丝扎水龙头找立诚叔要铁丝,他说对门是他叔家,大门没关,门楼底下就有铁丝叫我自己去拿,我去对门院子拿铁丝时,就感觉立诚叔的叔叔家跟别人家不一样可哪不一样又说不上来,当时拿到铁丝就回院给猪饮水也没在意。
往猪圈放水的时候,立诚叔可能被猪搅了酒兴心情大不爽,就一直对着猪圈骂骂咧咧,我爸洗了手说水让孩子放就行了你别唠叨了,他回了一声就扭头往屋走,这时就发生了一件很邪门儿的事:可能是没骂过瘾刚走两步就又转回来,咬牙瞪眼对着猪们“低开高收”的念叨了两句,我就站他旁边扶水管呢他念叨的什么我都没听清,但是!第一句最后一个字刚念叨完,所有正在围着喝水的猪一下就全都窜到猪圈角落里去了!挤在一堆打哆嗦!第二句最后一个字说完,那些猪全都原地一屁股坐趴地下了都能听见猪屁股整齐拍地“啪啦”的一片响,靠近我们这边儿的外围的几头都吓尿了!一点不假真尿了!叔吼完就陪我爸回屋吃饭了,直到我放满一整槽水,那些猪都还挤在角落里,我到堂屋门口往回看,猪们才敢陆续地过去喝水。
我们吃饭过程中立诚叔又把冰箱里的四瓶啤酒喝完了,新买的他嫌不够冰才没喝了,我们爷俩要走他非说要送我们回去!我爸熊了他几句喝了酒不要乱跑了才老实。
等我们回到家不忙了,才敢问我爸今天立诚叔把猪吓成那样怎么回事,老爷子也摇头,玩笑说也不知他练的什么功夫,又想起立诚叔对门儿的院子,反应过来哪里不对了:虽然只在门楼没进院,但那个院子是能一眼看完的,门楼到堂屋之间铺了一条砖道其它地方还是土地面,其它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了!农村人家的院子再收拾也得有堆有放各种家什儿杂物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过日子的样子”,像一般人家院子里自行车、电视天线杆子、自来水管、农用车、工具、煤球堆所正就是农村人过日子都得用的东西,那个院子里一概没有!干干净净,干净的一根草儿都没有!干净的让人能感觉异样!跟立诚叔家里相比正是两个极端,一个极其邋遢,一个过了分的干净整齐。
后来陆续听立诚叔说,他叔是个老单身汉从未婚娶,老头儿从年轻就自个儿收拾的倍儿精神利索,也不知每天忙啥,经常骑着摩托车早出晚归的,田间地头的活儿人家也没落下,但不管什么时候看到他,哪怕刚下地干活儿回来,老头儿身上身下鞋子袜子,倍儿干净利索!
回想起那天神奇的一幕,这叔侄二位也可谓邪门儿了!
图片来自网络,如有争议请联系删除。有没有什么超虐的短篇故事?
一个将性比作滑雪的故事。
一个晴朗冬日的中午……天气严寒,冻得树木喀喀作响。娜金卡挽着我的胳膊,两鬓的鬓发上,嘴上的茸毛上,已经蒙着薄薄的银霜。我们站在一座高山上。从我们脚下到平地伸展着一溜斜坡,在阳光的照耀下,它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。在我们身边的地上,放着一副小小的轻便雪橇,蒙着猩红色的绒布。“让我们一块儿滑下去,娜杰日达•彼得罗夫娜!”我央求道,“只滑一次!我向您保证:我们将完整无缺,不伤一根毫毛。”可是娜金卡害怕。从她那双小小的胶皮套鞋到冰山脚下的这段距离,在她看来就像一个深不可测的可怕地穴。当我刚邀她坐上雪橇时,她往下一看,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,连呼吸都停止了。要是她当真冒险飞向深渊,那又会怎么样呢?她会吓死的,吓疯的。“求求您!”我又说,“用不着害怕!您要明白,您这是缺少毅力,胆怯!”娜金卡最后让步了,不过看她的脸色我就知道,她是冒着生命危险作出让步的。我扶她坐到小雪橇上,一手搂着这个脸色苍白、浑身打颤的姑娘,跟她一道跌进深渊。雪橇飞去,像出膛的子弹。劈开的空气迎面袭来,在耳畔怒吼呼啸,凶狠地撕扯着我们的衣帽,刀割般刺痛我们的脸颊,简直想揪下你肩膀上的脑袋。在风的压力下,我们几乎难以呼吸。象有个魔鬼用铁爪把我们紧紧抓住,咆哮着要把我们拖进地狱里去。周围的景物汇成一条长长的,忽闪而过的带子……眼看再过一秒钟,我们就要粉身碎骨了!“我爱你,娜佳!”我小声说。雪橇滑得越来越平缓,风的吼声和滑木的沙沙声已经不那么可怕,呼吸也不再困难,我们终于滑到了山脚下。娜金卡已经半死不活了。她脸色煞白,奄奄一息……我帮着她站起身来。“下一回,说什么也不滑了,”她睁大一双布满恐惧的眼睛望着我说,“一辈子也不滑了!差点没把我吓死!”过了一会儿,她回过神来,已经怀疑地探察我的眼神:那句话是我说的,或者仅仅是在旋风的呼啸声中她的幻听?我呢,站在她身旁,抽着烟,专心致志地检查我的手套。她挽起我的胳膊,我们在山下又玩儿了好久。那个谜显然搅得她心绪不宁。那句话是说了吗?说了还是没说?说了还是没说?这可是一个有关她的自尊心、名誉、生命和幸福的问题,非常重要的问题,世界上头等重要的问题。娜金卡不耐烦地、忧郁地、用那种带有穿透力的目光打量我的脸,胡乱地回答着我的询问,等着我会不会再说出那句话。啊,在这张可爱的脸上,表情是多么丰富啊,多么丰富!我看得出来,她在竭力地控制自己,她想说点儿什么,提个什么问题,但她找不到词句,她感到别扭,可怕,再者,欢乐妨碍着她……“您知道吗?”她说,眼睛没有看我。“什么?”我问。“让我们再……再滑一次雪橇。”于是我们沿着阶梯拾级而上。我再一次扶着脸色苍白、浑身打颤的娜金卡坐上雪橇,我们再一次飞向恐怖的深渊,再一次听到风的呼啸,滑木的沙沙声,而且在雪橇飞得最快、风声最大的当口儿,我再一次小声说:“我爱你,娜佳!”雪橇终于停住,娜金卡立即回头观看我们刚刚滑下来的山坡,随后久久地审视着我的脸,倾听着我那无动于衷、毫无热情的声音,于是,她整个人,浑身上下,连她的皮手笼和围巾、帽子在内,无不流露出极度的困惑。她的脸上分明写着:“怎么回事?那句话到底是谁说的?是他,还是我听错了?”这个疑团弄得她心神不定,失去了耐心。可怜的姑娘不回答我的问话,愁眉苦脸,眼看着就要哭出来了。“我们是不是该回家了?”我问她。“可是我……我喜欢这样滑雪,”她涨红着脸说,“我们再滑一次好吗?”虽说她“喜欢”这样滑雪,可是,当她坐上雪橇时,跟前两次一样,她依旧脸色苍白,吓得透不过气来,浑身直打哆嗦。我们第三次飞身滑下,我看到,她一直盯着我的脸,注视着我的嘴唇。可是我用围巾挡住嘴,咳嗽一声,正当我们滑到半山腰时,我又小声说了一句:“我爱你,娜佳!”结果谜依旧是谜!娜金卡默默不语,想着心事……我从冰场把她送回家,她尽量不出声地走着,放慢脚步,一直期待着我会不会对她再说出那句话。我看得出来,她的内心怎样受着煎熬,又怎样竭力克制着自己,免得说出:“这句话不可能是风说的!我也不希望是风说的!”第二天上午,我收到一张便条:“如果您今天还去冰场,请顺便来叫我一声。娜。”从此以后,我和娜金卡几乎天天都去滑雪。当我们坐着雪橇滑下坡时,每一次我总是小声说出那句话:“我爱你,娜佳!”很快娜金卡对这句话就听上瘾了,就象人对喝酒、服吗啡能上瘾一样。现在缺了这句话她就没法生活了。当然,从山顶上飞身滑下依旧令人胆战心惊,可是此刻的恐惧和危险,反而给那句表白爱情的话平添了一种特殊的魅力,尽管这句话依旧是个谜,依旧折磨着她的心。受到怀疑的依旧是我和风……这二者中究竟谁向她诉说爱情,她不知道,但后来她显然已经不在乎了----只要喝醉了就成,管它用什么样的杯子喝的呢!一天中午,我独自一人去了冰场。我混在拥挤的人群中,突然发现娜金卡正朝着山脚下走去,东张西望地在寻找我……后来,她畏畏缩缩地顺着阶梯往上走……一个人滑下来是很可怕的,唉呀,可怕极了!她脸色白得象雪,战战兢兢地走着,倒象赶赴刑场一般,但还是走着,头也不回,坚决地走着。她显然打定了主意,最后要试一试,身边没有我的时候,还能不能听到那句美妙而甜蜜的话?我看到她脸色苍白,吓得张着嘴,坐上雪橇,闭上眼睛,仿佛向人世告别似地滑下去……“沙沙沙”……滑木发出响声。我不知道娜金卡是否听到了那句话,我只看到,当她从雪橇上站起来时已经摇摇晃晃、有气无力了。看她的脸色便可知,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听到什么没有,她一人滑下时的恐惧夺走了她的听觉,她已经丧失了辨别声音和理解的能力……眼看着早春三月已经来临……阳光变得暖和起来。我们那座冰山渐渐发黑,失去了原有的光彩,最后冰雪都融化了。我们也不再去滑雪。可怜的娜金卡再也听不到那句话,何况也没人对她说了。因为这时已听不到风声,而我正要动身去彼得堡----要去很久,也许一去不复返了。有一回,大约在我动身的前两天,薄暮中我坐在小花园里,这花园同娜金卡居住的那个院子之间,只隔着一道带钉子的高板墙……天气还相当的冷,畜粪下面还有积雪,树木萧条,但已经透出春天的气息;一群白嘴鸦大声呱噪,忙着找旧枝宿夜。我走到板墙跟前,从板缝里一直往里面张望。我看到娜金卡走出门来,站在台阶上,抬起悲凉伤感的目光望着天空……春风吹拂着她那苍白忧郁的脸……这风勾起了她的回忆;昔日,在半山腰,正是在呼啸的风声中她听到了那句话。于是她的脸色变得越来越忧郁,两行眼泪夺眶而出……可怜的姑娘张开臂膀,似乎在央求春风再一次给她送来那句话。我等着一阵风刮过去,小声说:“我爱你,娜佳!”我的天哪,娜金卡起了什么样的变化!她一声欢呼,笑开了脸,迎着风张开臂膀,那么高兴,幸福,真是美丽极了。我走开了,回去收拾行装……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如今,娜金卡已经出嫁。究竟是出于父母之命,还是她本人的意愿----这无关紧要,她嫁给了贵族监护会的一位秘书,现在已经有了三个孩子。想当年,我们一块儿滑雪,那风送到她耳畔一句话:“我爱你,娜佳!”----这段回忆是永生难忘的。对她来说,这是一生中最幸福、最动人、最美好的回忆……如今我也上了年纪,已经不明白,为什么当初我说了那句话,为什么要捉弄她……一个晴朗冬日的中午……天气严寒,冻得树木喀喀作响。娜金卡挽着我的胳膊,两鬓的鬓发上,嘴上的茸毛上,已经蒙着薄薄的银霜。我们站在一座高山上。从我们脚下到平地伸展着一溜斜坡,在阳光的照耀下,它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。在我们身边的地上,放着一副小小的轻便雪橇,蒙着猩红色的绒布。“让我们一块儿滑下去,娜杰日达•彼得罗夫娜!”我央求道,“只滑一次!我向您保证:我们将完整无缺,不伤一根毫毛。”可是娜金卡害怕。从她那双小小的胶皮套鞋到冰山脚下的这段距离,在她看来就像一个深不可测的可怕地穴。当我刚邀她坐上雪橇时,她往下一看,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,连呼吸都停止了。要是她当真冒险飞向深渊,那又会怎么样呢?她会吓死的,吓疯的。“求求您!”我又说,“用不着害怕!您要明白,您这是缺少毅力,胆怯!”娜金卡最后让步了,不过看她的脸色我就知道,她是冒着生命危险作出让步的。我扶她坐到小雪橇上,一手搂着这个脸色苍白、浑身打颤的姑娘,跟她一道跌进深渊。雪橇飞去,像出膛的子弹。劈开的空气迎面袭来,在耳畔怒吼呼啸,凶狠地撕扯着我们的衣帽,刀割般刺痛我们的脸颊,简直想揪下你肩膀上的脑袋。在风的压力下,我们几乎难以呼吸。象有个魔鬼用铁爪把我们紧紧抓住,咆哮着要把我们拖进地狱里去。周围的景物汇成一条长长的,忽闪而过的带子……眼看再过一秒钟,我们就要粉身碎骨了!“我爱你,娜佳!”我小声说。雪橇滑得越来越平缓,风的吼声和滑木的沙沙声已经不那么可怕,呼吸也不再困难,我们终于滑到了山脚下。娜金卡已经半死不活了。她脸色煞白,奄奄一息……我帮着她站起身来。“下一回,说什么也不滑了,”她睁大一双布满恐惧的眼睛望着我说,“一辈子也不滑了!差点没把我吓死!”过了一会儿,她回过神来,已经怀疑地探察我的眼神:那句话是我说的,或者仅仅是在旋风的呼啸声中她的幻听?我呢,站在她身旁,抽着烟,专心致志地检查我的手套。她挽起我的胳膊,我们在山下又玩儿了好久。那个谜显然搅得她心绪不宁。那句话是说了吗?说了还是没说?说了还是没说?这可是一个有关她的自尊心、名誉、生命和幸福的问题,非常重要的问题,世界上头等重要的问题。娜金卡不耐烦地、忧郁地、用那种带有穿透力的目光打量我的脸,胡乱地回答着我的询问,等着我会不会再说出那句话。啊,在这张可爱的脸上,表情是多么丰富啊,多么丰富!我看得出来,她在竭力地控制自己,她想说点儿什么,提个什么问题,但她找不到词句,她感到别扭,可怕,再者,欢乐妨碍着她……“您知道吗?”她说,眼睛没有看我。“什么?”我问。“让我们再……再滑一次雪橇。”于是我们沿着阶梯拾级而上。我再一次扶着脸色苍白、浑身打颤的娜金卡坐上雪橇,我们再一次飞向恐怖的深渊,再一次听到风的呼啸,滑木的沙沙声,而且在雪橇飞得最快、风声最大的当口儿,我再一次小声说:“我爱你,娜佳!”雪橇终于停住,娜金卡立即回头观看我们刚刚滑下来的山坡,随后久久地审视着我的脸,倾听着我那无动于衷、毫无热情的声音,于是,她整个人,浑身上下,连她的皮手笼和围巾、帽子在内,无不流露出极度的困惑。她的脸上分明写着:“怎么回事?那句话到底是谁说的?是他,还是我听错了?”这个疑团弄得她心神不定,失去了耐心。可怜的姑娘不回答我的问话,愁眉苦脸,眼看着就要哭出来了。“我们是不是该回家了?”我问她。“可是我……我喜欢这样滑雪,”她涨红着脸说,“我们再滑一次好吗?”虽说她“喜欢”这样滑雪,可是,当她坐上雪橇时,跟前两次一样,她依旧脸色苍白,吓得透不过气来,浑身直打哆嗦。我们第三次飞身滑下,我看到,她一直盯着我的脸,注视着我的嘴唇。可是我用围巾挡住嘴,咳嗽一声,正当我们滑到半山腰时,我又小声说了一句:“我爱你,娜佳!”结果谜依旧是谜!娜金卡默默不语,想着心事……我从冰场把她送回家,她尽量不出声地走着,放慢脚步,一直期待着我会不会对她再说出那句话。我看得出来,她的内心怎样受着煎熬,又怎样竭力克制着自己,免得说出:“这句话不可能是风说的!我也不希望是风说的!”第二天上午,我收到一张便条:“如果您今天还去冰场,请顺便来叫我一声。娜。”从此以后,我和娜金卡几乎天天都去滑雪。当我们坐着雪橇滑下坡时,每一次我总是小声说出那句话:“我爱你,娜佳!”很快娜金卡对这句话就听上瘾了,就象人对喝酒、服吗啡能上瘾一样。现在缺了这句话她就没法生活了。当然,从山顶上飞身滑下依旧令人胆战心惊,可是此刻的恐惧和危险,反而给那句表白爱情的话平添了一种特殊的魅力,尽管这句话依旧是个谜,依旧折磨着她的心。受到怀疑的依旧是我和风……这二者中究竟谁向她诉说爱情,她不知道,但后来她显然已经不在乎了----只要喝醉了就成,管它用什么样的杯子喝的呢!一天中午,我独自一人去了冰场。我混在拥挤的人群中,突然发现娜金卡正朝着山脚下走去,东张西望地在寻找我……后来,她畏畏缩缩地顺着阶梯往上走……一个人滑下来是很可怕的,唉呀,可怕极了!她脸色白得象雪,战战兢兢地走着,倒象赶赴刑场一般,但还是走着,头也不回,坚决地走着。她显然打定了主意,最后要试一试,身边没有我的时候,还能不能听到那句美妙而甜蜜的话?我看到她脸色苍白,吓得张着嘴,坐上雪橇,闭上眼睛,仿佛向人世告别似地滑下去……“沙沙沙”……滑木发出响声。我不知道娜金卡是否听到了那句话,我只看到,当她从雪橇上站起来时已经摇摇晃晃、有气无力了。看她的脸色便可知,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听到什么没有,她一人滑下时的恐惧夺走了她的听觉,她已经丧失了辨别声音和理解的能力……眼看着早春三月已经来临……阳光变得暖和起来。我们那座冰山渐渐发黑,失去了原有的光彩,最后冰雪都融化了。我们也不再去滑雪。可怜的娜金卡再也听不到那句话,何况也没人对她说了。因为这时已听不到风声,而我正要动身去彼得堡----要去很久,也许一去不复返了。有一回,大约在我动身的前两天,薄暮中我坐在小花园里,这花园同娜金卡居住的那个院子之间,只隔着一道带钉子的高板墙……天气还相当的冷,畜粪下面还有积雪,树木萧条,但已经透出春天的气息;一群白嘴鸦大声呱噪,忙着找旧枝宿夜。我走到板墙跟前,从板缝里一直往里面张望。我看到娜金卡走出门来,站在台阶上,抬起悲凉伤感的目光望着天空……春风吹拂着她那苍白忧郁的脸……这风勾起了她的回忆;昔日,在半山腰,正是在呼啸的风声中她听到了那句话。于是她的脸色变得越来越忧郁,两行眼泪夺眶而出……可怜的姑娘张开臂膀,似乎在央求春风再一次给她送来那句话。我等着一阵风刮过去,小声说:“我爱你,娜佳!”我的天哪,娜金卡起了什么样的变化!她一声欢呼,笑开了脸,迎着风张开臂膀,那么高兴,幸福,真是美丽极了。我走开了,回去收拾行装……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如今,娜金卡已经出嫁。究竟是出于父母之命,还是她本人的意愿----这无关紧要,她嫁给了贵族监护会的一位秘书,现在已经有了三个孩子。想当年,我们一块儿滑雪,那风送到她耳畔一句话:“我爱你,娜佳!”----这段回忆是永生难忘的。对她来说,这是一生中最幸福、最动人、最美好的回忆……如今我也上了年纪,已经不明白,为什么当初我说了那句话,为什么要捉弄她……公众号《从刺沉默》还有更多小说



